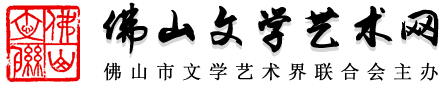奶奶最后一次去她家的情形,我至今仍记得一清而楚。那是一年中最令人心烦的日子,从北方一路杀过来的寒流,到了这里,遭遇埋伏,被太平洋上来的暖湿气流团团围住,进退两难。雾气从清晨一直弥留到夜晚,太阳半个月也不肯露一次脸,衣服干不透,总带着一股酸溜溜的味道,阳台的花盆里,偶尔还会长出一朵红蘑菇呢。 记得那天是星期六,吃过午饭,我抱着靠垫,像萝卜一样陷在沙发里看电视,脑子像灌满浆糊,昏昏欲睡。奶奶在帮我洗碗,洗到一半,突然火急火燎地跑出来,手上抓着一把湿答答的筷子,好像煤气瓶快要爆炸一样。她说:“小欣,快,快,快给我找个红包。” 鞋柜上方的抽屉里塞满了花花绿绿的宣传纸,大多是房地产和美容院的广告,这些都是奶奶的宝贝,吃饭前,她会抽出一张,折成四方的小盒盛骨头和菜渣。就在那里,我找到了一个红包,不过,它皱巴巴的,像被人揉过一样。 奶奶接过去,眉头立刻皱成两团赤黑的墨。我以为她嫌太旧,谁料她竟说:“这,这也忒小了。”我被她逗乐了,嬉皮笑脸地说:“凤姐,用大红包装五块钱,就像潘长江穿姚明的西装,你也不怕人笑话?”我奶奶大名陈家凤,开玩笑的时候,我总管她叫凤姐,她倒也不生气。她伸出干枯的手指,在我面前晃了晃说:“要包三千块咧。”她的话让我吃惊不已,我不解地看着她说:“你疯了?”她没理我,解下围裙,笑眯眯地从兜里掏出一叠钱,手指蘸了蘸口水,不紧不慢地数起来。 这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激活了我沉睡已久的八卦之心,我把客厅翻了个遍,最后在一本过期的《ELLE》杂志中找到一个大红包。我兴冲冲地把红包给她,她竟又叹起气来。“还太小?”我有些不耐烦。她瘪了瘪嘴说:“这上面写的‘恭喜发财’,要是‘新婚快乐’就好了。”一听到结婚两个字,我就更八卦了,笑兮兮地问:“谁结婚呀?就是我结婚你也不会封这么大的红包吧!”她没接我的话,自言自语道:“就是替她去死,我也愿意。”我一听,知道谁要结婚了。她叹了口气,眼圈就像插上电的电热丝一样,开始慢慢变红。我知道她马上又要一把鼻涕一把泪了,赶紧像吓唬小孩一样吓唬她:“你要是再哭的话,等一下我就不陪你去了。” 这一招果然管用,她回到房间,从箱子最底下翻出一条紫色的绸棉袄,上面印着大朵大朵的牡丹花。那是她认为最漂亮的一件衣裳,平时舍不得穿,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会翻出来。我一走近,闻到一股浓烈的樟脑味,鼻子痒痒的,刚想说话,就开始打喷嚏,一连打了三个。我揉了揉鼻子说:“穿这么厚的衣服,你就不怕化了?”她也不示弱,回了一句:“又不是冰棒,怎么会化掉呢?”我无奈地摇了摇头,蹲下来,帮她换鞋。 外面雾气很重,天地之间白茫茫的一片,就像一个澡堂子,马路对面的楼房像是被人偷偷拆掉了,一点痕迹都未留下。 她家在城北,我家在城南,本来,坐地铁可以直达,只需要四十多分钟,可奶奶却不乐意,她从不坐地铁,她说只有死人才在地底下穿来穿去,又说,万一要遇上地震想跑都跑不掉。在这件事情上,她非常固执,我只好牵就她,这也意味着我们在路上至少需要花一个半小时。 我有一个习惯,一上车就会睡觉,车子晃得越厉害,我睡得越沉。不仅如此,我还做了个梦,梦到了她。她去世九年来,我经常会梦到她,梦中总是阳光灿烂,她总是笑眯眯的,拉着我的手,给我买漂亮的公主裙,带我玩摩天轮,去吃哈密瓜味的冰淇淋。她没有孩子,但特别喜欢孩子,尤其是我。每次分开时,她都有些不舍,要我叫她一声妈妈。而这一次,却是下雨天,傍晚时分,天色很暗,恍如午夜,我走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。风很大,卷起屋檐上的瓦片,重重地摔下来,声音大得吓人。在一条的拐角处,我看到一个女人,一只脚穿了木头拖鞋,另一只脚光着,苍白如同大理石。她浑身都淋湿了,抱着手臂,头埋得胸前,像被人砍掉了一样。我很害怕,头皮发麻,跑了起来。就在这时,我听到背后传来一个凄惨声音:“为什么不来看我?......为什么不来看我?......为什么不来看我?”我听出是她的声音,一回头,她却不见了......我吓出一身冷汗,醒了过来。我发现奶奶也睡着了,身子缩成一团,打着呼噜。 下车后,我们钻进了一条小巷弄,那里像猪肠子一样弯曲、湿滑,到处都是黑得发绿的污水,墙壁上贴满了老军医的广告,有人用白粉笔写下的“随地小便,没收工具!”。刺鼻的气味一路尾随着我们,我只好捂住鼻子。巷子寂静而颓败,一个人都见不到,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错觉——我们正朝一片荒凉的墓园走去。不知道走了多久,奶奶终于在一幢苍白的水泥房子前站住了。 我认出那棵芒果树,它比先前更粗更高。芒果树下,是一个斜披的铁皮小屋,黑乎乎的屋子里,摆着烟酒、糖果和饼干,柜台上蒙着一层灰。有一个胖女人在睡觉,她仰着头,嘴巴张得很大,一张苍蝇飞进去,又飞了出来。店门口,堆满了杂物,有剥了皮的电线,有一叠叠的废纸盒,还有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塑料瓶......在这些杂物中间,放着一张果绿色的小方凳,看到它,我心里不禁一阵悸动,像看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友。九年过去了,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。 楼梯间很黑,一进去,就像被人蒙住了双眼。楼道几乎被旧家具占满了,有的地方,需要侧身才能通过。空气里弥漫着木头腐烂的味道。我扶着奶奶。突然,一个毛绒绒的东西嗖的一下从我脚尖掠过,我吓坏了,尖叫起来,不敢再往前走。看到我大惊小怪的样子,奶奶说:“一只老鼠,就把你吓成这样,真没出息。”我回了一句:“你又不是不知道,我最怕的就是老鼠了。” 刚走到二楼,奶奶站在那里,像被人点了穴。我问她:“你......不舒服吗?”她紧紧抓着我的手说:“我们,我们,还是回去吧。”声音很轻,好象受了很大委屈似的。 在车上晃了那么久,到了门口,她却改变了主意。我的肺都快被她气炸了,但还是像哄小孩一样问她:“怎么了?你哪里不舒服?”她像做错了事情一样,低着头,紧咬着嘴唇,眼泪骨碌骨碌滚下来,用最小的声音说:“钱......钱被偷了。” 我在她的外套里找了一遍,又把裤子口袋都翻出来了,可是,里面半包纸巾,一张乘公交的老年人卡,还有一颗真滋味棒棒糖。我安慰她:“是不是刚才忘记带出来了?”她一言不发,布满老年斑的两只手像嫌疑犯一样低垂着头,在接受审问。我说:“我身上有三百块,行不行?”她摇了摇头。我咬了咬牙说:“现在去银行取钱,总可以吧?”她没吭声。我下楼,她跟着下楼,我让她在楼下等,她不肯,执意要跟在我身后。 从银行取完钱往回走,太阳竟然蹦出来了。士多店的胖女人还没醒来,毛绒绒的阳光照在她身上,像盖了条黄色的床单...... 我想起九年前她弥留的那个晚上,奶奶带着我来做最后的道别——奶奶佝偻着腰,一只拿着手帕,一只手拄着拐杖。走几步,就要停下来,用手帕抹一下眼睛。我的心怦怦直跳,血管里像有一列火车,窜东窜西,完全失去了方向。到了楼下,只见她家灯火通明,但很安静,像是一家人出去散步忘记了关灯。我扶着奶奶上楼梯,奶奶的身体轻极了,像纸糊的一样。楼道里有一股花露水味道,越往上走,味道越浓,我闻到被花露水掩盖着死亡的味道,就像茂密的草丛中间躺着一条毒蛇。门虚掩着,像一张病恹恹的脸。我的小腿不由自主地擅抖起来,颤抖很快传遍了全身,我听到牙齿碰撞发出的清脆声响。奶奶推开门,光线刺痛了我的眼睛,就在这时,我听到无比痛苦的声音——类似于鸽子发出的咕咕声,那应该是从她喉咙里发出来的。我拔腿就往楼下跑。我不敢回头,总觉得身后有一只手,要来抓我的头发。士多店的灯光让我感到安全,胖女人的笑容让我觉得温暖,我就坐在那张果绿色的方凳上,跟一条脏兮兮的土狗玩。夜色越来越沉,不知道过了多久,窗户里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,我低着头,不敢再看...... 她家门上贴着一个烫金的喜字,上面挂满水珠,它们慢慢滑落下来,留下长长的尾巴,像一行行眼泪。我轻轻敲门,心仍怦怦直跳,好象她还弥留在屋里,还在发出痛苦的咕咕声。 等了好一会,没有人来开门。“不会出去了吧?”我随口说道。奶奶一听,着急了,忙用力拍打着门,边拍边喊,庆春!庆春!声音很响,像是来讨债一样。又过一会儿,我听到屋子里发出哐当一声,可能是一只搪瓷杯掉在地上。 一阵踢踢塔塔的拖鞋声之后,门开了一条缝。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秃了顶的男人,瘦高瘦高,穿了一套浅灰色保暖内衣,领子野了,无精打彩地耷拉着。他打着呵欠,露出黑黄的牙床,像一排发了霉的老玉米。我叫了一声“姑父”,这个词太久未讲,像是一块生锈的铁,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别扭。 见到我们,他一脸意外,愣了一下,结结巴巴地说:“妈,怎么是你?……你,你们怎么来了?……怎么,怎么也不先打个电话?我,我好去楼下接你。”“我买菜的时候,碰到你大姐,才知道的”,奶奶顿了顿,又埋怨道,“这么大的事,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?!”他不知道怎么回答,像根旗杆一样,傻傻地竖在门口,一时竟忘记了请我们进屋,奶奶穿过他的腋窝,像穿山甲一样钻进了屋。姑父一脸歉意,让我们先坐一会儿,自己回卧室换衣服去了。 眼前的一切,已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了。地上铺了仿古的瓷砖,木条窗换成了铝合金窗,小阳台上放了一张摇椅,我记得,那里原先堆满了杂物,角落里有一个木头的狗窝,小狗点点在她去世之后,也离家出走,再没回来。屋里的摆设也大不相同了:以前的餐桌是红漆的木桌,一条腿还绑了铅丝,现在换成了气派的大理石餐桌,上面摆着一只陶瓷花瓶,瓶子里,蓝色的满天星围绕着五朵淡黄色的百合花;以前的沙发,是从工厂里搬来的,包了一层绿色的绒布,像黑乎乎的苔藓,现在换成了酒红色的皮沙发,沙发上搁着几个豹纹的靠垫......空气里到处充满了喜气。只是,她的气息,一丁点都找不到了。 几分钟后,姑父终于出来了,他换上了粉色的短袖衬衣和卡其色的西裤,显得精神了许多,但脚上仍趿着那双臧青色的夹趾拖鞋。 奶奶上下打量了一番说:“你别说,你这身打扮还真让我想起第一次见你的样子了。” 姑父说:“哪里,都老啦。” 奶奶抬起头,想了一会说:“那得有多少年啦?” 姑父说:“快三十年了。” 奶奶叹了口气说:“是啊,时间过得真快,一晃她都走了九年了。” 我赶紧用胳膊肘轻轻碰了她一下,她回过神来,忙说:“不说这些了,不说了。你看,我真是老糊涂了。”她飞快用衣角擦了擦自己的眼睛,轻声问:“你......一个人在家吗?” 姑父嗯了一声,声音很小,只是喉结轻轻颤动了一下。 奶奶顿时像是变了一个人,腰板挺得直直的,说话时,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。她站起身,像领导一样视察起来,她推开每一个房间的门,在里面转上几圈,好象在找什么人,又好象在找什么东西。一边看,一边还自言自语:“都是新的,多漂亮,多好看,什么东西都是新的好啊。” 主卧的床是新添置的,很大,差不多占去了半个房间。紫色的蚊帐,层层叠叠,像欧洲宫廷里的样式,很长,垂在地上。被褥是浅紫色的,上面印了许多小碎花,双人枕头旁边,躺着一盒避孕套。 奶奶摸了摸床沿问:“这床很贵吧?” “不......不贵,一点都不贵。” “要不要五千块?” “我哪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,五千块可以买三张了。” 她又用手按了按床垫,最后,竟然一屁股坐在了上面。她说:“太软了,对腰可不好!” 他笑着点头。 她又用指关节敲了敲梳妆镜,问:“这是实木的吧?” “不是,哪里买得起实木呢,全是木屑压出来的。” “最好还是买实木的,要不然这样的天气很容易发霉,别看它现在漂亮,一发了霉就难看了。” 我看到姑父一脸的尴尬,忙说:“又不是在一楼,不会发霉的。” 奶奶没有接我的话,她正抬头看着梳装镜上方的那面空墙,看了好一会儿。我也好奇地凑上前,墙上什么东西也没挂,只不过,有一个不规则的小窟窿,可能是钉子拔掉后留下的。天花板上挂着水珠,过一段时间就会往下掉一颗,有一滴正好滴到了奶奶的眼睛里,她开始揉起了眼睛。姑父站在她身后,舔了舔嘴唇,搓了搓手,显得很不自在。我终于想起来,那里原来是挂结婚照的。我仿佛看见扎着两条辫子的她正在朝我们微笑。 奶奶对屋子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。在主卧,她打开了衣橱,看了看挂在里面的衣服,衣服飘出一股浓烈的香水味,把她呛得直打喷嚏。在厨房,她打开折叠桌上的饭罩,看看他们中午吃了些什么菜,菜式很简单,芹菜炒肉丝、芙蓉蛋,还有一小碟五香豆腐干。最后,她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,一句话也不说。姑父坐立不安,满脸堆着肥皂泡一样的笑,说:“妈,我……我给你泡茶。”奶奶点了点头。我看到她额头上全是汗,有一撮头发紧紧贴在额角,像一只灰壁虎。我说:“把外套脱了吧?”奶奶没理我。 煮水的时候,大家都没什么话说,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闷起来,大家都看着那个不锈钢的电热水壶。我听到老式电冰箱发出刺耳的嗡嗡声,听到挂钟发出机械的咔咔声,听到风吹过时玻璃窗的抖动声。我想到她躺在床上的最后时刻,那些空空荡荡的下午,家里没有其他人,只有这些枯燥乏味的声音陪伴着她。在最后的时刻,她一定想见一见我,让我再叫她一次妈妈,可我却不敢靠近她。她如此疼我,我却对她如此残忍。想到这里,鼻子不禁一酸。 幸好,水滚得很快,骨碌骨碌地响着。姑父不紧不慢地起身,从冰箱里取出一小包铁观音,从茶几上取了茶壶和三只青花小瓷杯,开始洗杯子。他先将杯子泡在滚水里,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杯沿,飞快地旋转着。茶泡在壶里,他还不停地用热水,给它洗淋浴。空气里开始弥漫淡淡的茶香。大概半分钟后,他开始倒茶,淡黄色的茶汤盛在雪白的瓷杯里,很好看。 他用两只手将茶捧给奶奶,奶奶接过来,眼睛却盯着他的手指。他右手戴着一个金戒指,上面刻了一个“福”字,锃亮、闪烁、刺眼。他或许感觉到奶奶目光中的异样,把右手收回来,用左手盖住。 看到这一幕,我又想起了她来,心里不禁一阵酸涩。她是奶奶唯一的女儿,一辈子都在吃苦,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,最值钱的也只是一枚银戒指。奶奶不止一讲跟我提起关于她的往事。姑父家的条件不好,她嫁给他的时候,奶奶坚决反对,将她反锁在家里,但她性子很硬,以绝食相逼,整整四天,没吃一点东西。眼看着她只剩下最后一点微弱的呼吸,奶奶只好妥协。婚后,他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很清苦,工厂的效益本来就不好,后来,又发生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,厂长携款而逃,工厂倒闭了,他们两人同时失去了工作。那些年,姑父就在街边接零活,她在家里给人缝补衣服。也就是第二年冬天,她被查出患上了乳腺癌。家里太穷,没钱去大医院,她就找了一些中药的偏方来煲,那段时间,整个厨房都被熏黑了,苦涩的中药味,钻进了墙壁的缝隙里,久久不能散去。后来,病情越来越严重,姑父准备卖肾送她去医院,但一切都晚了...... “明天准备摆多少围呢?”奶奶喝了口茶问。 “六围”,姑父顿了顿,低着头,补充道,“主要......是她那边的亲戚。” “好象少了点。” “我本来不想摆,可她非要摆。” “还是摆吧,结婚毕竟是大事。” “老了,无所谓了。” “在哪里摆呢?” “福满楼。” “我去那里吃过饭,听说很贵,要多少钱一桌?” “不贵。” “要不要一千五?” “不用。” “一千块总要吧?” “差不多吧,我也不知道。” “对了,你母亲今年有八十了吧?” “八十二了。” 奶奶哦了一声:“她明天会去吗?” “她上个月不小心摔了一跤,把骨头摔断了,下不了床,住在我大姐家。” 奶奶叹了口气说:“她还是比我有福气啊!”她的语气中,竟生出一丝淡淡的嫉妒。 ...... 他们就这样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,奶奶好象什么都关心似的,而姑父的回答,总像外交官一样小心谨慎。 不知不觉,暮色从窗户里缓慢地爬了进来。隔壁传来炒菜的声音,清脆、悦耳。姑父抬头看了一下钟,时间已近六点。他起身去开灯。灯光照亮的一瞬间,我心里咯噔了一下,这让我禁不住想起电影散场的时刻。奶奶或许和我有同样的感受,她脸上有一丝不易觉察的伤感与眷恋。姑父说:“要不,晚上就在这里吃饭吧?”奶奶忙说:“不用了,”她顿了顿,笑着说,“下次……下次吧。” 奶奶拿出红包,放在茶几上,轻轻拍了拍说: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,祝你们新婚快乐。”姑父愣了一下,皱着眉头,好象很生气的样子说:“妈,你这是干什么?你的钱我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收的。”奶奶笑眯眯地说:“钱是少了点,你别嫌弃就行。”姑父拿起红包往奶奶的口袋里塞。奶奶板着脸说:“庆春,你要是不收,我可就生气啦!”姑父的语气软下来,几乎是在恳求:“妈,你的心意我领了,钱你还是快收起来吧。” 他俩正在推搡,有人敲门,声响很大,整个房子都在震颤,我头顶的水晶吊灯慌乱起来,发出丁丁当当的碰撞声。姑父跑去开门,一阵尖声尖气的咒骂声传进来:“你耳朵聋啦!我在楼下叫了你半天,你怎么也不应一声?我的手都快拎断了。你就知道睡觉!”姑父媚笑着接过五六个沉甸甸的袋子,低声说:“家里......来客人了。”女人进屋了。她长得五大三粗,脸绷得紧紧的,上面打了厚厚的粉底,白得吓人。姑父放好袋子,赶紧找了双拖鞋,递到她跟前。她刚染完头发,一股刺鼻的染发剂味道,在房间里发散开来,我的鼻子一阵阵发痒,想打喷嚏,却打不出来。屋子里的气氛有些凝滞。 姑父有一些慌乱,他急忙介绍说:“这是......”奶奶接过话头说:“我是他姨妈......远房的,听说你们要结婚,特意过来送份子。这个是我孙女。”我看到奶奶佝偻着腰,显得单薄而又瘦小,刚才飞扬在她脸上的神采,早已烟消云散。一听说我们是来送钱的,女人立刻像变了个人,干巴巴的脸顿时舒展开来,像一片茶叶掉到了开水杯里。奶奶把红包塞给她,她一点也不推辞,用粗短的手指捏了一下。 奶奶准备告辞,她赶忙拉着她的手说:“这都到吃饭的时间了,怎么还走呢?我下去买几个菜,你们晚上就在这里吃饭。”奶奶说“下次,下次吧。”女人说:“那怎么行呢?这样说出去要让人笑话的。”奶奶说:“都是自己人,不客气的,我家里还有事。”女人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奶奶说:“真有事?”奶奶说:“真的。”女人也不客气了,马上说:“那我就不勉强了,明天晚上记得早点来喝喜酒啊。”奶奶一听,脸色突然变得煞白,手捂住胸口,但她还是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说:“好!”。 门关上了。楼道像漆黑的地窖。奶奶回过头,像是在做最后的道别。她有气无力地说:“小欣,我走不动了。”我弯下腰,背上她,两只手紧紧抓住她,怕一松手她就会像鸟儿一样飞走。我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湿了,水滴到唇角,带来一阵轻微的凉意。雾又开始重了。
(发表于2014年第2期《十月》,入选《2014-2015广东中短篇小说精选》)
(盛慧。男。1978年生于江苏宜兴,著有长篇小说《白茫》、散文集《风像一件往事》、诗集《铺九层棉被的小镇》等,曾获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提名、《人民文学》“新世纪散文奖”,首届广东省青年文学奖。现为佛山市艺术创作院专业作家。)